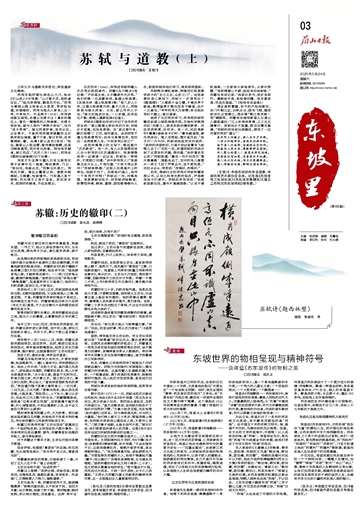□四川成都 鱼化龙 胡婷婷
敢谏敢言罪宰相
苏辙对自己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,深感失望。一气之下,他以父亲在京修《礼书》,兄长出仕凤翔,傍无侍子为由,奏乞留京养亲,辞不赴任。
在凤翔任职的苏轼得知弟弟辞官决定,写诗《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》劝慰苏辙,不同意他辞官的轻率决定。苏辙和诗《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》为自己辩解,他在诗中说:“怪我辞官免入商,才疏深畏忝周行。……闭门已学龟头缩,避谤仍兼雉尾藏。”虽然自己已经“学龟头缩”“兼雉尾藏”,但是留京侍父只是借口,他的内心仍然孤傲,坚持己见,不肯低头。
英宗治平二年(1065)正月,苏轼结束在凤翔的任职,还朝判登闻鼓院,又试秘阁再入三等,得直史馆。于是,苏辙留京养亲的理由不再成立,他向朝廷乞官外任。苏辙被朝廷任命为大名府(河北大名)推官,不久出任管勾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。
哥哥苏轼可谓平步青云,弟弟苏辙却在边远之地,担任小小的幕僚,从事繁琐的文字伏案工作。
治平三年(1066)四月,苏洵在京师逝世,苏轼、苏辙兄弟护送父亲灵柩,自汴河入淮,顺长江回到家乡眉山。次年十月,葬父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。
神宗熙宁二年(1069)二月,苏轼、苏辙兄弟服丧期结束后,返回京师。此时,朝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,神宗皇帝励精图治,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,推行新法,这就是著名的“王安石变法”。
变法之初,诸法未备,神宗诏求直言。
苏辙见年轻的神宗大有作为,不禁欢欣鼓舞,他奋笔疾书,一道《上皇帝书》,洋洋洒洒近万言。他在上书中说:“夫财之不足,是为国之先务也。”,欲治国必先理财,苏辙抓住根本,深入分析当前国家形势,“夫今世之患,莫急于无财而已。财者为国之命,而万事之本。国之所以存亡,事之所以成败,常必由之。”查找导致国家危机的原因,“故臣谨为陛下言事之害财者三:一曰冗吏,二曰冗兵,三曰冗费。”要解决危机,就必须任用贤能,大胆改革。“君臣同心,上下协力,磨之以岁月,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。”苏辙慷慨陈词,虽然是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,但毕竟属于越次言事,内心诚惶诚恐,不知这道奏折上去,会不会又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?
哪知神宗看完苏辙上书,大为欣赏。即日破格在延和殿召见苏辙,听取他关于改革丰财的意见,并任命苏辙为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。
制置三司条例司是“王安石变法”组建成立的一个临时性机构,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。三司条例司任用吕惠卿、曾布、苏辙等官阶低微的年轻人,参与草拟新法。
对于苏辙这个青年才俊,王安石开始对其寄予厚望。
变法伊始,他曾就“青苗法”的实施,约见苏辙,无比诚恳地表示:“有任何不宜之处,请直说无妨”。
苏辙拿到新法的草案,仔细研读了一番,只回了王大人五个字:“看上去很美”。
王安石当然不服:“此话怎讲?”
苏辙马上答辩:“政府出钱,贷给百姓,即便良民,也难免乱用,逾期还款者,定有很多。州县衙门,又得耗费人力物力,催租逼债。”
王安石脸色一黑,苏辙却视而不见,继续慷慨激昂:“前朝刘晏执政,从不放贷于民。但四方丰歉、谷价贵贱,他都了然于胸。贵时抛售,贱时收购,所以物价稳定,百姓富足。这种‘常平仓’法,极为有效,为何不用?”
王安石微微颔首:“你说的有点道理,容我再想想。”
然后,就没了然后,“青苗法”实施照旧。
没过多久,王安石急于知道新法成效,便派人前往陕西,估算朝廷获利。
州县官吏,为讨上级欢心,纷纷夸大其词,虚报数字。
苏辙听说后,当即致信王安石,直言条例司欺上瞒下,贻笑天下,再次痛斥“青苗法”之弊,力阻新政推行。他直接上书神宗《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》,表示反对。王安石大为恼怒,将加罪于苏辙,因副相陈升之的反对才作罢。苏辙一不做二不休,上书《条例司乞外任奏状》,请求离开条例司外任。
苏辙时年三十岁,仍然年轻气盛。他身处变法大本营,只要稍加留意,依附顺从王安石,仕途青云直上是没有问题的。他的同事吕惠卿、曾布、章惇等人后来都步步高升,贵为宰相。当然,苏辙二十多年后也担任了宰相,不过这升迁的道路也未免太曲折了。
话说神宗皇帝看完苏辙言辞激烈的奏章,感觉疑惑不解,问王安石:“辙与轼如何?观其学问颇相类。”
安石曰:“轼兄弟大抵以飞钳捭阖为事。”帝曰:“如此,则宜合时事,何以反为异论!”(《续资治通鉴》)
显然,神宗是支持王安石的。而王安石说苏轼兄弟“飞钳捭阖”即好出风头,邀功进赏的意思。这就完全曲解苏辙的赤胆忠心了,苏辙看见一项危及老百姓利益的政策即将出台时,奋不顾身为民请命,其精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。幸好神宗并未同意王安石加罪苏辙的建议,准予苏辙离开三司条例司。
秋末,苏辙在三司条例司待了短短五个月时间被迫离开。时张方平知陈州(河南淮阳),聘任苏辙为州学教授。这是苏辙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,一个锐意进取,勇于改革的优秀青年,转眼间被时代抛弃,划入到反对变法阵营,甚至成为旧党的中坚力量。
苏轼对弟弟受到的挫折深表同情,经常写诗去信问候。
熙宁四年(1071)十一月,苏轼也因反对新法出判杭州,他在《戏子由》诗中写道:“宛丘先生长如丘,宛丘学舍小如舟。常时低头诵经史,忽然欠伸屋打头。”虽为安慰弟弟,但苏轼仍然改不了他好开玩笑的习惯。“文章小技安足程,先生别驾(杭州通判)旧齐名。如今衰老俱无用,付与时人分重轻。”他们两人都才三十来岁,哪里谈得上衰老,但苏轼对弟弟说公道自在人间,不要灰心丧气。“门前万事不挂眼,头虽长低气不屈。”面对打击,我们更要坚持读书人的风骨。这首《戏子由》后来也成为苏轼讽刺新法的证据之一。
苏辙的好友文同对苏辙也很关心,二人常有书信往来。文同到陵州任太守时,作《子瞻〈戏子由〉依韵奉和》寄给苏辙,诗中写道:“子由在陈穷于丘,正若浅港横巨舟。每朝升堂讲书罢,紧合两眼深埋头。”,“贫且贱焉真可耻,欲挞群邪无尺箠。”对那些欺负苏辙的小人,他恨不得拿起尺箠(鞭子)加以痛打!“安得来亲绛帐旁,日与诸生共唯唯。”虽然苏辙的年龄比文同小得多(二十岁),但文同表示愿意当他的学生。“君子道远不计程,死而后已方成名。千钧一羽不须校,女子小人知重轻。”文同认为苏辙为道义而献身的精神非常可贵,这一点就是妇女儿童都是明白的。
(鱼化龙:《国防时报》社媒体运营副总监兼主任,系中国散文学会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、四川省作协会员;胡婷婷:网络作家。)